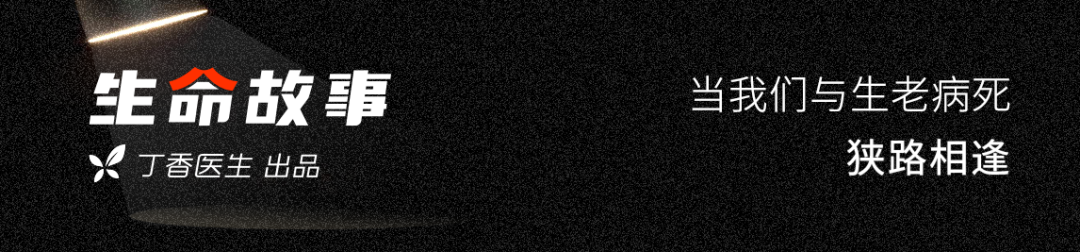
路过人间,我们都不免与生老病死狭路相逢。这是丁香医生的第 39 个有关生命的真实故事。
「张爱娟?」
「到!」
「徐建国?」
「他又去厕所了,护工刚刚去推他呢。」

在庭院参加每日例会的患者
图片来源:作者提供
阳棚下,二十几位身着常服的患者正围成一圈,坐在各自的轮椅上进行每日例行的点名。圈子中间站着一位医生,手里拿着病历板,板上夹着一张皱皱巴巴的点名单。
「这是我们心理医生。」身穿红条纹衣服的老太太开口了,「他很会搞花头,每天掐着人数开会。哪天人没齐,他准去病房找那些个没来的,更新到他的名单上。」
这番话并非只是对我这个外来人的介绍,字间蕴藏更多深刻意味——在这里,每天都会有老朋友悄然离世。
徐医生手上的那本点名单,其实是一张「生死簿」,而那些被划掉的名字,其实是刚刚离开人世的患者。
这些仍在庭院里点名答到的老人,此前大多已被医院下了「死亡通知书」,来到这座院子里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。
这里是北京松堂关怀医院——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,也是第一家让患者「等死」的医院。

中国第一家让患者「等死」的医院
死亡是灰色的,但松堂是彩色的。
患者们把家中的被褥带来,病房里就有了百家百户组成的颜色。每间病房的门口挂着橙色的专属铭牌,每个铭牌都来自一所大学或一个社会组织,标注着点对点的志愿者服务信息。

病房走廊的橙色铭牌,每个病房对应几个志愿单位
图片来源:松堂 30 周年纪念短片截图
走廊尽头的病房传来虫鸣,一张空床的床头柜上摆着两只蛐蛐儿,它们正交替用力地用高分贝身体诉说着些夏日的情绪。
「这是我们李院长送给这床患者的蛐蛐儿,这床的患者生前很喜欢蛐蛐儿,院长就时常买了蛐蛐儿带来。通常,这些小生命都活不过 100 天,但院长送来的蛐蛐儿平均都能活 120 天以上。」
现在,最后两只「长寿」蛐蛐儿们还活得好好的,主人却已离开人世。

病房床头柜上的蛐蛐儿
图片来源:作者拍摄
宫廷风的房梁,黄红相间的大阳棚,灰色的小雕像……松堂像个清朝遗留的王府,庭院里立着个大阳棚,池子里的喷泉溅起阵阵彩虹。医师节刚过,八月炎热的暑气似乎并没有侵袭到这里。
据工作人员介绍,「这些都是李院长的设计。为了让医院看起来更丰富些,他甚至搬来了许多家中的收藏,用来装点医院的工作区域」。
在楼下病人的集会里,我见到了人们口中的「李院长」,李伟。
面前的李伟 70 多岁,是个一米八几的大高个。他正穿着一身素净的白衣黑裤熟练地穿梭在老患者中间,一会组织大家唱东方红,一会背唐诗宋词,顺便还给几个单身的老患者牵上了红线。

陪患者逗乐的李伟
图片来源:作者拍摄
「他就是嘴贫」,被李伟牵线的老太太曾经是新中国最早一批初中教师,「别看他现在瞎牵线,他为人可正经得很。前几天,他还组织为我们院里的一对钻石婚的老夫妻举办了庆祝仪式。」
也许是疾病的缘故,许多老人的神情常常呈现一种淡漠的状态,但经李伟唠上几句后,很快就喜笑颜开。
在这家让患者「等死」的医院,一切似乎都是鲜活的样子。
但与院内乌托邦般的静谧不同,李伟和松堂的故事,残忍而坎坷。

第一个「吃螃蟹」的人
上世纪七十年代,年轻的李伟在内蒙古农村担任赤脚医生一职,那时,他和同是北京下放的一位教师私交甚好。
「张老师很敬业,我很敬重他。后来,县里的医生说他身上长满了瘤子。」有从医经验的李伟知道,这是癌症晚期。
从医院回来后,李伟坐在好友的床边,两人默契地刻意避开生死话题,谈天说地。
「那时候,他很兴奋,特别愿意说话,但讲着讲着就突然停住了。他告诉我,最近一直在回想走过的路,觉得自己一生都在为人民服务,一直在做好事,可到头来却连个人的称号都没有。」
彼时,张老师这样被下放到农村的教师,被叫做「牛鬼蛇神」,「他像小孩子一样,眼泪哗哗地流。」
思维出走的关头,李伟心一横,决定撒一个谎。「他是个好人,临死前不应该这么痛苦。隔天,我告诉他,公社领导已经同意了他的平反,他不是牛鬼蛇神,他是一个正正当当的人。」
好友闻言,一把拽住李伟的胳膊,眼里噙满泪水,「早上九点撒的谎,张老师当天夜里十一点多去世。这段时间里,他一直鼓着掌,带着微笑,反复呢喃自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。」
这件事给李伟带给了很大的震撼。「生前他那么痛苦,以泪洗面,却因为几句宽解变得那么灿烂,完成了生命最后的成长。」
在好友的墓前,一颗种子在李伟的心中悄悄种下。
文革结束后,李伟带着临终关怀事业的理想回到北京,却被所有人当作「外星人」。
那个时期,医院都由国家一手包办,以福利性和计划经济为主,医疗只能勉强满足基本的生命需求,没有人有做临终关怀的经验,「年富力强的人还缺医少药,搞临终医院这是在胡闹啊。」
直到八十年代中期,国家宣布开放民营办医,李伟决定辞去稳定的工作,给心里那颗在好友墓前播下的种子松松土。
他要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
政策松绑,民营医院从无到有,但专门做临终关怀的医院还是一家都没有。
没有可参考的样本、没有同样心怀抱负的同僚、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意见,成立这样一家理想化的专科医院难于登天。「别说没人做这一行,大家压根就不知道这一行。」
临终关怀医院不好开,那就先开一家有临终关怀的医院吧。李伟决定「曲线救国」。
他卖掉了收藏的限量版猴票,攒了一笔钱,联系上从北大医院退休的老医生,提出建立「北京联合专家医院」的想法:他出资建院,为退休医生提供再就业环境,老医生们负责提供专业技术和金字招牌。
在这里,李伟借着自己董事的身份,用钱换来了话语权。
2 个病房,6 张病床,临终关怀科室成立,隔壁的邻居成了第一名患者。
李伟的邻居是乳腺癌晚期,全身多发转移,医院没法治,被安排出院。
「我告诉大哥,我们医院可以帮他照顾嫂子,能帮打止痛针,一直陪伴她到临终,不会让她强制出院。」

现在松堂医院的病房走廊,与普通医院并无二异
图片来源:作者拍摄
然而,在其他同事眼里,临终关怀科室是一个燃烧热情却不能回本的地方,总干「没用又不讨好的活儿」。
医院的的其他内外科室每月都可以维持几万元的收入,但李伟的病房一不开刀,二不卖常规药,几乎是入不敷出。
每次开会,大家都劝李伟放弃临终关怀科室,做回全科医生,「认真为医院搞创收,民营医院赚钱和治病一样重要。」
各部门还打起了配合站,李伟的开药权限首当其冲。他经常遇到各种止痛药间歇性断供应的情况。
「我看到药物就躺在药柜里」,但药房总以提前预约、药物紧张为借口塘塞回去。「医院并不是没药,只是不想给我用。不挣钱的活儿,没有人支持。」
医院是追逐生命的地方,如何有成本拥抱死亡?
9 个月后,医院开始盈利运营,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僚们选择对李伟摊牌——院务会一致决定,撤掉李伟投资的股份,「爱干嘛干嘛去,医院负担不起这么高的情怀」。
意料之外,情理之中,初创人员成了被驱赶的「赔钱医生」。李伟带着撤出的股份,和科里的 2 个医生、4 个护士一起,离开了这块伤心地。

四处漂流的医院,先后 7 次搬家
李伟一路往郊区走,来到香山。
一年 16 万租金,十年长约,最早的松堂关怀医院在香山部队医院的外壳里落地成型。

李伟和松堂医院的雏形
图片来源:松堂 30 周年纪念短片截图
在普通人的认知里,香山环境清幽、山清水秀,是一个再适合不过的「临终场所」。可放在上世纪 80 年代,这样的假设并不成立——香山距离主城区几十公里,道路尚是泥路,建设较差,家属来回至少需要 7 小时,十分不便。
天亮出发,日暮才能回,给拥有正常工作的家属们造成了很大的生活困扰。
而对于临终的患者,相比环境的清幽,家人们的亲情显然更重要。因此,不断有家属强烈要求医院搬迁至离城区更近的位置,甚至,他们纷纷提出离院诉求。
无奈之下,医院再次选址新院区,松堂开始了四处漂流的日子。
在香山的最后一天下午,食堂被最后启动,大师傅们给所有人蒸了热腾腾的大包子,买了些啤酒,计划带去新院区供一顿犒劳的夜宵。
100 多个轻症病人暂时出院回家,李伟和其他几个医生一起,压着最后一辆救护车和六七个重病人,赶往新院区......

松堂医院的救护车,正准备出车去接患者入院
图片来源:作者拍摄
打开车门的瞬间,李伟愣住了。上百个居民自发用肉体堵上了院区大门,包围着松堂的搬迁车辆,拒绝所有病人下车。
原来,「松堂关怀医院」的牌匾一放在新院区门口,就引起了轩然大波,「死人医院进社区」的消息传遍了街头巷尾。
「这是死人医院,天天死人,天天送葬,太晦气了!这是八宝山前一站,他们来了,我们这辈子都发不了财!」一个 30 来岁的小伙子在人群中大喊,「叔叔阿姨们,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。如果今天让他们搬进去了,以后就赶都赶不走了!」
中国人对于生死的忌讳揉进了骨子里,居民们推攘着,带头的几个妇女指着患者骂街,胆大的男人直接上手打砸医院物什,抽出一个办公桌抽屉往空铁床上抡。
场面陷入僵局,李伟报了警。但这并不是警察能管的治安问题,他们也爱莫能助。
年轻的医生把救护车里病情比较重的病人抬出来透气,马路牙子上,十来个病人躺在担架上一字排开,对面是居民熙熙攘攘的人头,另一伙抗议的群众正气势汹汹地带着蒲扇往这里赶。
终于,治安管理的人员也来了:零点前要求搬离。
那时,已经十一点一刻了。
一个全程参与物资搬运的年轻大夫听到这个消息,半月以来积攒的疲惫瞬间变成泪水决堤而下。他低声抽泣着,「我们怎么这么难啊?」一句哭声引出了一片哭声。
没有手机的年代,10 个医生护士拿着老北京的电话大黄本,四散在公用电话亭向北京所有的医院逐个电话求助。40 分钟后,每一个人都带着被拒绝的沮丧回到车队。
其实,医院的行为不难理解。这些患者入院后不需要进行治疗性操作,重病患一住就是小半年,由于国家没有针对安宁疗护的特殊政策,这样长期压床会直接导致科室绩效的降低。
关键时刻,李伟只能一拍脑袋,得出下策中的上策:搬回香山。
30 万一口价,租金翻一番,换一年安生地。
李伟让食堂的大师傅把夜宵大包子分发给工作人员,拦下了路边十多辆小面包后,走向了返程的回头路。
往后的 16 年里,这家土生土长的民营医院又因为经济、政策等原因等先后经历 7 次搬家,没有哪次称得上容易。

生死教育:年轻的力量
在长期的被动里,松堂医院努力钻研出一些主动的新思路。
「我们走到现在,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帮助。」李伟心中充满感激,「首先就是那些提供志愿服务的学生。在香山的时候,一群北大学生春游,误进了我们医院,见到这些老人后,就主动提出留一个下午陪伴他们。」
李伟意识到,对于患者来说,人与人之间的关心才是无与伦比的温暖;而对这些学生来讲,没有哪一节生死教育课会比直面死亡来得更深刻。
于是,他悄悄动起「互动」的念头。
大部分情况下,运营一家民营医院,需要预支相当一部分的资金用于宣传。临终关怀医院不同于普通医院,虽然患者享有医保,但国家却没有针对医院自身的补助。
同时,由于不以治愈为目的,医院没有过多的医学用药与创伤性治疗,所有的收入都来源于患者的「包月医养服务费」,每人每月 5000 元。
空出来的资金缺口,只能靠医院自己填——没有钱,那就做不花钱的宣发。
李伟决定,与北京各个高校的学生党支部、学生会、红会等建立联系,申请将医院申请作为学生志愿者生死教育基地的试点单位。
「我们欢迎每一位来松堂提供服务的志愿者。我们不会用医生的身份说教,通过和临终患者的接触,学生们可以真实体会到死亡。这种亲身经历他们心中留下的震撼,远比我们口述来得强。」

与老人交流的年轻学生
图片来源:松堂 30 周年纪念短片截图
基于临终关怀的跨学科属性,很多大三的学生开始把毕业设计的主题放在这里,松堂医学课题组的工作人员则积极接受采访、提供信息,从专业领域出发,提供临终关怀事业的研究数据。
相应地,这些毕设也成了松堂的「自来水」宣传。

与首都医科大学共同撰写《临终关怀学》
图片来源:松堂 30 周年纪念短片截图
深刻的生死教育,结合自成一派的临终关怀理论体系,松堂成立的十年后,李伟受邀去 200 多所大学举办讲座。
和主动成立志愿者试点单位的思路相同,他选择不收讲课费用。「作为临终关怀行业的从业者,承担生死教育的社会责任是我的义务。如果这样的行为可以让大家更关注到我们医院,关注到这个行业,就是两全的最好办法。」
终于,这样的宣传模式诱发蝴蝶效应,松堂尽到了临终关怀「老大哥」的角色,这些宣传也为松堂带来了社会效益。

中央电视台对李伟和松堂医院的专访
图片来源:松堂 30 周年纪念短片截图
多年后的某个午后,倾斜柔和的日光切进病房,轻轻盖在一位病重患者身上。
伴随着稍有些拥挤的嬉笑声,几个十来岁孩子接连走进来,团团围住病床。
「奶奶,这是我们从峨眉山带回来的蝴蝶标本。」
「奶奶,您这身衣服真好看。」
「奶奶,我期末考了一百分!」
叽叽喳喳的你言我语间,热烈的生命力被压缩在这个小小的空间。
听着大家的交谈,观赏完一支口琴表演,老人脸上的皱纹里溢出满足,化作泪水流转在眼眶,她缓缓举起架在被子上的两只沉重手臂,轻轻鼓起掌来。

志愿者的表演后,开心鼓掌的老奶奶
图片来源:松堂 30 周年纪念短片截图

生命的延伸
朝阳一隅,李伟和松堂迎来第 17 个年头。
从没有政策支持及人民认可的时代走到现在,一步一个泥坑,李伟削尖了脑袋,那颗在好友墓前埋下的种子终于长成了大树。
在夕阳的余晖里,李伟带我聆听松堂特别的低吟。
走廊尽头是一间幽暗的屋子,墙边摆放着一张病床,床上铺着几张全新的治疗巾,床的四角立着四朵泛红光的莲花,这是患者临终后的助念室。

助念室的特殊病床
图片来源:作者拍摄
在松堂,每天都有 2~3 人在医院里去世,太平间容量却极其有限。
为了减少尸体的滞留率,也为了增加人文关怀,医院会为每一位死去的患者预设祭奠时间和空间。家属们来到祭奠房间,可以完成传统送葬仪式的悼念部分,此后尸体会被直接送去火葬场。
那些有特别需求的患者则会被送到助念室,用家属希望的方式送完亡者最后一程。
在李伟看来,人们对于死亡的认知不是消亡,而可以变成一种生命的延伸,「这不是迷信,对于有需要的患者来说,这可以成为一种生的寄托。」

松堂 30 周年纪念短片截图
图片来源:作者拍摄
截至 2017 年 6 月 13 日,全国设有临终关怀科的医疗机构共 2,342 家,而据《「中国城市临终关怀服务现状与政策研究」总报告》推算,全国每年需要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病人超过 750 万。
即使已经三十年过去,如今,临终关怀医院的发展依然供不应于求。
「我们需要更多的松堂,」李伟轻轻总结。

松堂庭院里的屏风
图片来源:作者拍摄
松堂的庭院里,静静立着一块屏风:我们要活 120 岁。
(文中张爱娟、徐建国系化名)
本文转载自丁香园
作者 carollero
内容审核 gyouza
封面图来源 站酷海洛

